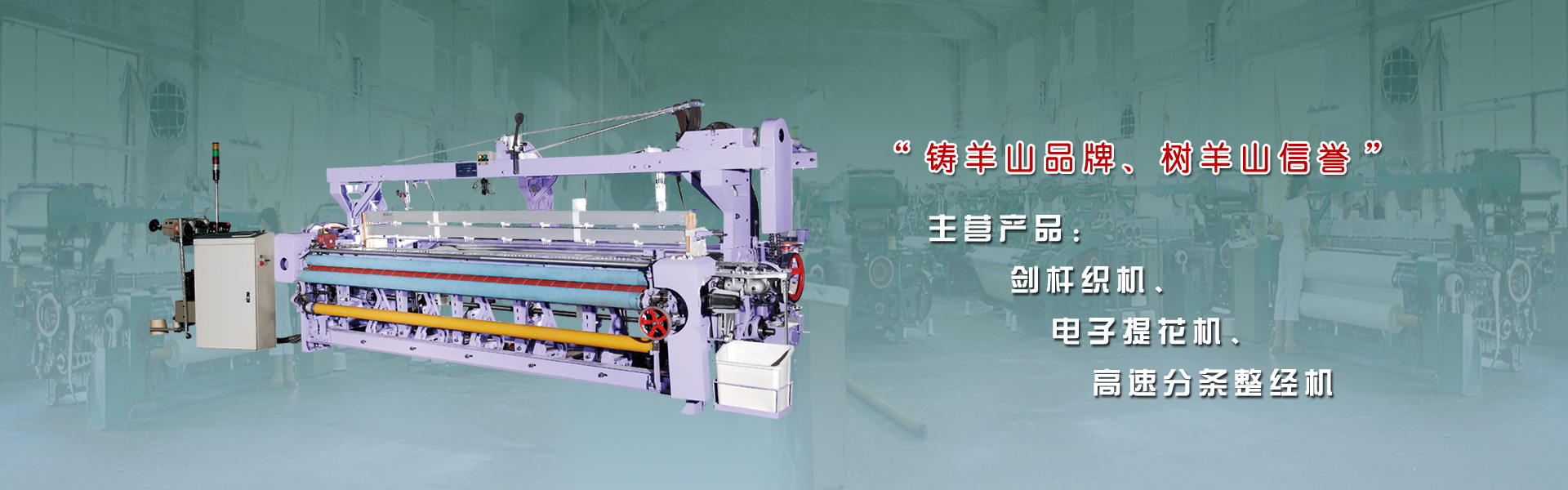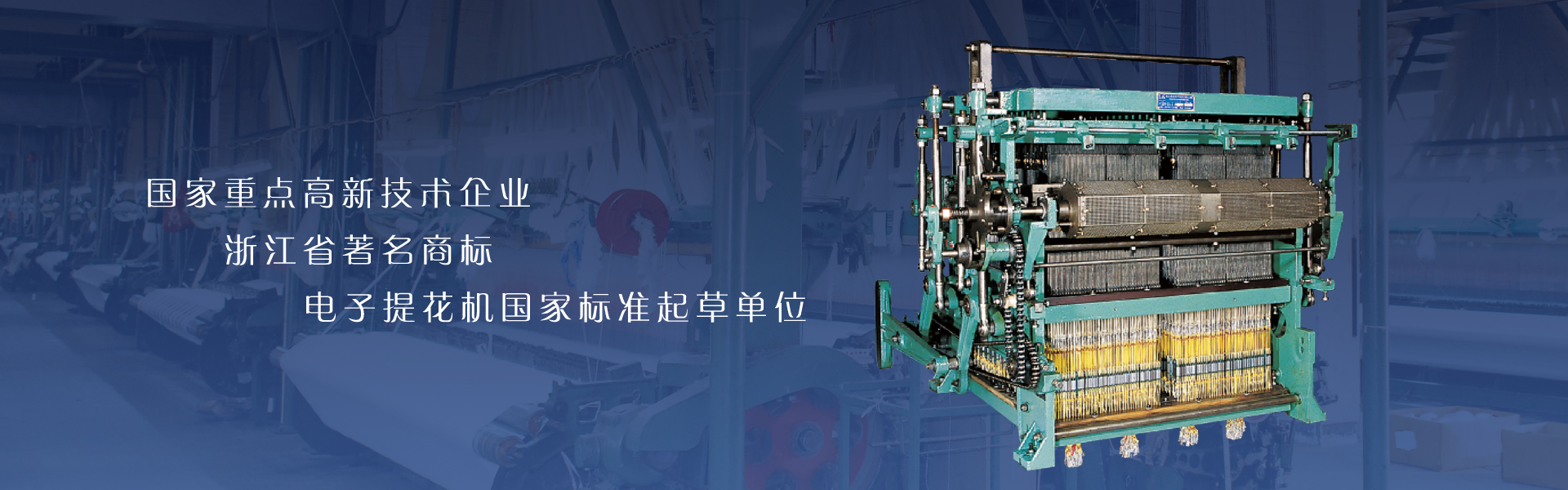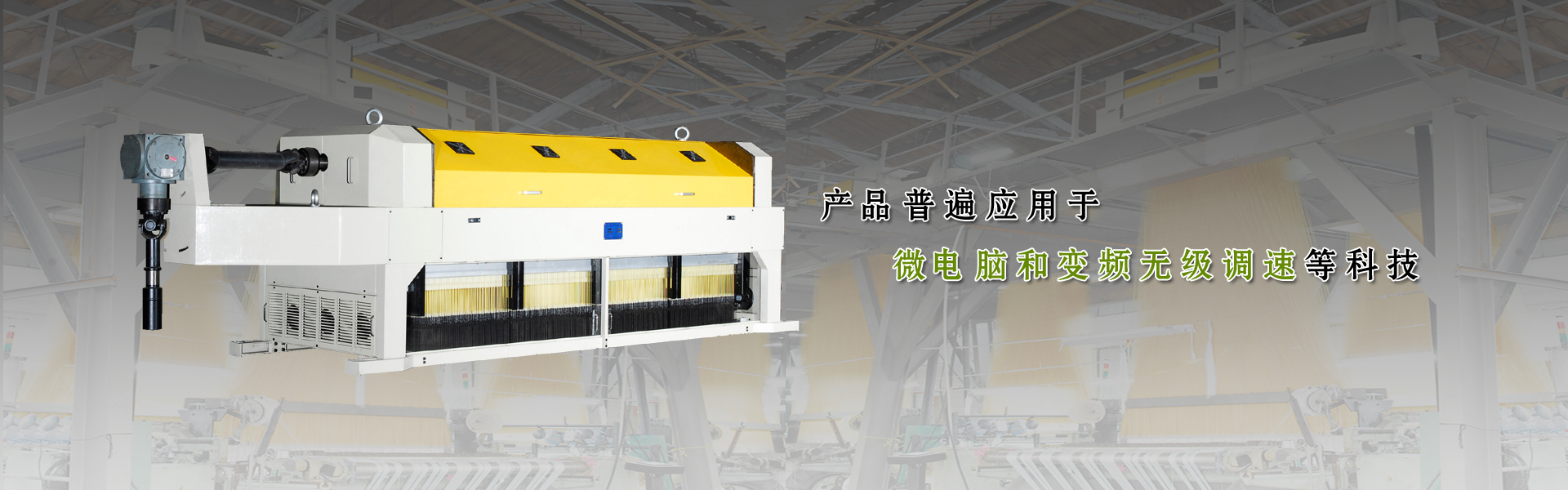【新华每日电讯】我国木拱桥:“只此青绿”间长虹凌空起
清流激湍,映带着两岸的山岭村舍,溪涧之上是一座座古拙的木拱桥,交流着路途,也连接着人心。它们被誉为“桥梁制作活化石”,有如一颗颗明珠,散落在浙南闽北的山水之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维护非物质文明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5日将“我国木拱桥传统营建技艺”项目从急需维护的非物质文明遗产名录转入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标志着这一技艺的系统性维护取得了明显成效。
桥下两水交汇,桥上飞檐斗拱,桥体的红漆已显斑斓,廊顶的灰瓦久经风雨,在温州市泰顺县,全国重点文物维护单位北涧桥是游客打卡的必经之地,不少游客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山水田园中的廊桥,美得像梦境相同。”
在丽水市庆元县,同为“国保”的如龙桥依山而建,贯穿南北。工匠奇妙地依托北侧的山势,在桥北端修起钟楼,有如翘起的龙尾,在桥南端修筑桥亭,有如低俯的龙首,而桥中的廊屋房顶,又有如拱起的龙身。“如龙桥”由此得名。这样的木拱桥,在浙南闽北山区有上百座。由于桥上建有遮风避雨的廊屋,又常被称作“木拱廊桥”。古往今来,农民牵着耕牛在桥上走过,母亲领着孩子在桥上走过,外出务工、经商、肄业的游子也在桥上走过。
这样的木拱桥,还从前给学者以极大的惊喜。《清明上河图》的一画之眼便是汴京城里,横跨汴河的虹桥。“其桥无柱,皆以巨木虚架”的建桥方法曾令茅以升、唐寰澄等老一代桥梁学家赞叹不已。可是,有很长一段时刻,学界都认为这种技能已失传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在浙南闽北地区发现,相似的技能不光没有失传,还有什物存在。上海交通大学规划学院木结构修建研讨中心主任刘杰教授说,闽浙木拱桥与汴梁虹桥有相相似的当地,但又具南方木构修建特征,汴梁虹桥的木构件间用绳子捆扎,而木拱廊桥则采用了更为精巧的榫卯结构。
1996年,刘杰仍是同济大学的一名研讨生二年级学生,跟从导师路秉杰去泰顺调查古修建。在回温州的山路上,他和同学坐在车里被颠得头昏脑涨,只听得教师一声大吼:“泊车!这里有座桥,我得下去看看。”
等他们理解过来,路秉杰现已跑到了桥的另一端。回头看到两个学生毫无反响,教师大为不满。“他说咱们两个人有眼无珠,看到那么好的木桥,居然无动于衷。”
从那时起,刘杰就开端了木拱廊桥的研讨之路。他和记者说,在学术研讨中称它们为“编木拱”结构更为精确。工匠不需要用特别长大的木材,而是用木构件织造成大跨度的桥拱,跨过浙闽山区的深溪。“木拱跨度最长能有40多米,而赵州桥也只要37米。”
20世纪80年代,为了鄙人游水库扩建后保住上游的古廊桥,庆元县博物馆老馆长吴其林掌管了兰溪桥的异地迁建。他曾回忆说,桥面最底下一层是箬叶,第二层是木炭,第三层又是箬叶,第四层才是沙石料,这样的桥面防潮吸水。而为了撤除已有400多年前史的木拱架,工人们还用上了千斤顶和起重葫芦。
“编木拱极为精巧,足够表现了我国人的营建才智,它的制作方法是现在最先进的‘模块化装配式集成修建’的前驱。”刘杰和记者说,工匠要用三根木头和五根木头搭成名为“三节苗”和“五节苗”的两类支架,作为桥拱的中心,再用横向的木头(牛头)交叉起来,纵横紧密咬合,使桥身极为巩固。“‘三节苗’还能起到梁的效果,假如更精确地说,这样的桥还能够叫‘编木拱梁桥’。”
只要用15根筷子,就能搭起一座承重两三斤的木桥,这是“90后”庆元人胡俊峰小时候常玩的游戏。教会他这种游戏的,是胡俊峰的父亲、国家级非遗项目“木拱桥传统营建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胡淼。而这种游戏始于何时,当地白叟也只知道“自己小时候就会玩”。
1983年,胡淼跟着父亲胡永德走上了兰溪桥的迁建工地。2022年,胡俊峰从上海回到家园庆元,跟从父亲学习造桥。在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的胡俊峰一直在协助父亲收拾材料,制作成CAD图纸。“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又教给我,木拱桥的修建技艺一定要传承下去。”
而泰顺县至今流传着全民救廊桥的佳线日,受飓风影响,当地三座“国保”级廊桥被暴升的洪水冲垮,不到一周的时刻,三座古桥的原木构件有90%就被沿岸大众找回。2017年,经过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同意,在当地多位非遗传承人的掌管下,三座廊桥完成了修正。
记者从浙江省文明广电和旅行厅得悉,2009年,浙闽两省联合申报“我国木拱桥传统营建技艺”被列入急需维护的非物质文明遗产名录。泰顺、庆元两县作为维护地,均出台了系列扶持维护方针,并在2023年联合拟定了《廊桥维护三年行动计划》。温州市还为廊桥维护专项作了当地立法。现在,浙江已有非遗代表性传承人21人,共有木拱桥传统营建技艺实践团队170多人。
“我最早看望过的一批老工匠大都现在现已过世了,其时学界就很忧虑会不会后继乏人,这也是其时这一项目列入‘急需维护名录’的终究的原因。经过15年的尽力,当地经过方针鼓励,现已培育出了一批木拱桥营建技艺的传承人。”刘杰说,“他们不光在当地造桥,还去外地造桥。现在,许多当地都喜爱制作木拱廊桥,这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表现了咱们的文明自傲。”“此次‘转名录’,标志着我国木拱桥传统营建技艺从‘急需维护’进入到‘正常维护’,完成了良性循环,代表了国际社会对项目维护传承成效的高度认可,也表现了我国政府高质量地履行了《维护非物质文明遗产条约》。”浙江省非遗维护协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二级教授陈华文说。